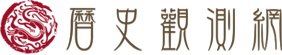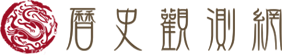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,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,它们分别被称为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。
《左传。昭公十二年》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说:“良史也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这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,《左传》历代注家都说是“古书名”,贾逵说:“三坟,三皇之书;五典,五帝之典;八索,八王之法;九丘,九州亡国之戒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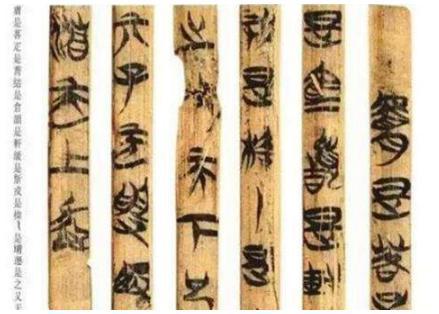
郑玄说,“三坟五典”就是“三皇五帝之书”。楚灵王说这话的“昭公十二年”是公元前530年。可否由“能读”,推断“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是前代的文字读物。
据说是孔子撰写的《尚书序》则称:“伏牺(羲)、神农、黄帝之书,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(尧)、虞(舜)之书,谓之《五典》,言常道也。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,虽设教不伦,雅诰奥义,其归一揆,是故历代宝之,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,谓之《八索》,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,谓之《九丘》;丘,聚也,言九州所有,土地所生,风气所宜,皆聚此书也。”
问题是,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“坟”、五帝时代的书称为“典”、伏羲时代的书称为“索”、帝禹时代的书称为“丘”?
《尚书序》的回答是“坟”有大的意思,“典”有常的意思,“索”有求的意思,“丘”有聚的意思。据说是孔子撰写的《尚书序》则称:“伏牺(羲)、神农、黄帝之书,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(尧)、虞(舜)之书,谓之《五典》,言常道也。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,虽设教不伦,雅诰奥义,其归一揆,是故历代宝之,以为大训。八卦之说,谓之《八索》,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,谓之《九丘》;丘,聚也,言九州所有,土地所生,风气所宜,皆聚此书也。”
显然,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,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。
在相当一段时间里,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《尚书序》的说法,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,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。然而,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(参阅笔者所著《符号之谜》一书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),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《山海经》的考证,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《山海图》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(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,这项工作已完成,包括42平方米的《帝禹山河图》),笔者开始意识到“坟”、 “典”、“索”、“丘”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。